那么,德雷福斯究竟是何人?德雷福斯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中,普鲁士(后来的德国)占了上峰。法国遭遇惨败,不仅失去了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地区,还深刻影响了法国的民族自信心,导致了极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间谍活动的过度敏感。
自1871年法国第三共和国创立以来,法国政坛贪腐现象日益严重,政府高层官员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的事件层出不穷。在这一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些在法国金融界拥有显著影响力的犹太银行家被指控参与了与政客勾结的腐败活动。这种情况导致保守派社会精英对犹太人群体展开了猛烈抨击,他们声称政府的腐败行为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犹太人的操控,这一论调进一步加剧了军界和整个社会的反犹情绪。
到了1894年,反犹主义情绪在法国社会愈发弥漫,特别是在军事界。一些军官持有贵族和君主主义的思想,他们对外界的“间谍活动”充满警惕,而统计局(Statistics Section)则负责进行反间谍工作。该机构由让·桑德尔(Jean Sandherr)领导,桑德尔本人有着明显的反犹情感,这种偏见在其工作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时,法国约有8万名犹太人,其中大约4万人居住在巴黎,另外4.5万名则分布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等地。媒体在这一时期的反犹情绪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著名的反犹主义记者埃杜阿尔·德吕蒙(Édouard Drumont)便是这股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坚决主张“军队中的犹太人正在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并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这一观点。早在1889年,德吕蒙就联合一批持保守立场的天主教虔诚信徒以及主张对德国复仇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共同组建了一个被描述为“丑恶且热烈”的反犹联盟。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其理念,该联盟于1892年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言论自由报》(La Libre Parole),试图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将法国的犹太人及其影响力彻底清除出法国社会。该报在1892年达到20万份的发行量。德鲁蒙于1886年出版的《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一书,也成为了煽动反犹情绪的工具,首年销量达到15万册,为当时的反犹主义情绪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德吕蒙及其众多追随者经常高举“法国只属于法兰西民族”的口号,这一表面上爱国的宣言背后实则隐含着更为危险的意图,那就是“干预法国事务的犹太势力必须被彻底铲除”。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也为后来爆发的德雷福斯事件埋下了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这一时期的反犹情绪不仅仅是针对个别涉嫌腐败的犹太人,而是演变成了对整个犹太群体的系统性排斥,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深层次的民族认同危机和社会矛盾。
法国军队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成了这场系统性反犹主义灾难的牺牲品。
1859年,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地区穆卢兹(Mulhouse)的相当富裕的犹太家庭。他比赫茨尔大半岁。1870年普法战争后,他的家乡被割让给德国,但其家人选择移居巴黎,保持法国国籍。他在巴黎理工学院接受教育,后加入法国陆军,成为一名炮兵军官,并最终晋升为总参谋部的上尉。
1894年9月中下旬,法国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份“边栏文件”(bordereau),该文件列出法国军事机密,内容涉及火炮和防御计划,疑似已经泄露给德国。文件在德国大使馆的废纸篓中被发现,笔迹被初步比对后指向德雷福斯。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被逮捕并秘密监禁,罪名是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1894年12月19日至22日,德雷福斯在军事法庭接受了第一次审判,庭审闭门进行,基于伪造的证据和笔迹专家的意见,他被一致定罪。判决书称其“叛国罪成立”,判处终身流放。
前面讲的1895年1月5日在巴黎军事学院举行的“军阶褫夺仪式”就是对德雷福斯判决执行的一部分。当天,犹太记者赫茨尔恰好赶到现场进行报道,目睹了整个仪式的全过程。赫茨尔和诺尔道当时都相信德雷福斯会真的背叛了法国,毕竟那些通敌的证据都“令人信服”。但是,德雷福斯的“军阶褫夺仪式”对赫茨尔和诺尔道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场令他震惊令他作呕的历史悲剧。尤其是对赫茨尔来说,这一仪式不仅让他感到无法理解,更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虽然赫茨尔没有在他当年的日记中如此承认,但在他日后的回忆中,他说,正是目睹德雷福斯被羞辱被褫夺军阶的场景,促使他在认知和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致于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当时,那些围观的人群涌上街头、激烈地喊着口号,声音中充满了深深的愤怒与仇恨。赫茨尔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耳朵,因为人群不是在叫喊“德雷福斯去死”、“间谍去死”,而是在叫喊“犹太人去死”!赫茨尔完全觉醒了:那些法国人的愤慨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人,也不是针对象德雷福斯这样的所谓“间谍”,而是针对整个犹太民族!赫茨尔就象掉在冰窟窿里一样感到浑身的寒颤,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场景!霎那间,他意识到:“无论我们犹太人多么地想同化、多么地想融入这些国家,但在欧洲人的眼中,我们永远是不受欢迎的异类!看来,解决反犹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我们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
这个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呢?
当时的德雷福斯漫画
这时,赫茨尔开始聚精会神地思考这个问题。他擅长剧本创作,这使他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将自己脑海中关于建国的构想以脚本的形式写出来。为了不受外界干扰,赫茨尔把自己关在公寓里,连续五天不断写下自己的思考与计划。他的一名朋友前来探访时,看见赫茨尔衣衫褴褛、神情狂乱,顿时感到惊愕万分。朋友建议他出去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并劝他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否则他可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但赫茨尔对此并不在意,他依旧坚持自己的信念,要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向全世界的犹太人宣告。
再说“军阶褫夺仪式”之后不久,被法国人称为“犹太间谍”的德雷福斯上尉,于同年2月21日经法国兵舰押送至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Devil's Island)。经过几个月的航行,他在同年4月抵达魔鬼岛,并在那里被单独监禁。(more words here✌)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赫茨尔,德雷福斯事件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的影响,使他意识到犹太人面临的困境与迫害需要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因此,他决心将犹太复国的千年理想付诸实践。他奋笔疾书,写了又写、改了又改。不过,让他真正全身心地投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是随后不久发生的另一件重要事件。
1895年3月,赫茨尔返回奥地利。在维也纳,他发现整个城市正深陷危机之中,气氛紧张,形势严峻。


%E4%B8%8E%E2%80%9C%E6%91%A9%E8%A5%BF%E4%B9%8B%E5%AD%90%E2%80%9D%E6%88%90%E5%91%98%E5%90%88%E5%BD%B1%20-%20Copy.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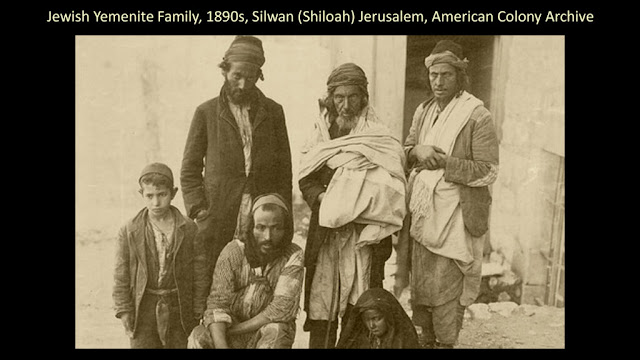



%E7%9A%84%E5%88%9B%E5%A7%8B%E4%BA%BA%E5%85%B9%E7%BB%B4%C2%B7%E8%B5%AB%E5%B8%8C%C2%B7%E5%8D%A1%E5%88%A9%E8%88%8D.jpg)
%E7%9A%84%E5%88%9B%E5%A7%8B%E4%BA%BA%E6%91%A9%E8%A5%BF%C2%B7%E8%B5%AB%E6%96%A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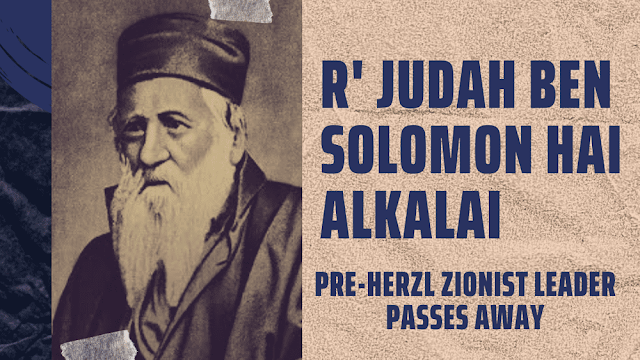




%E7%9A%84%E3%80%8A%E6%B6%88%E5%A4%B1%E7%9A%84%E7%BD%97%E9%A9%AC%E3%80%8B%E7%B3%BB%E5%88%97%E7%BB%84%E7%94%BB%E4%B8%AD%E7%9A%84%E4%B8%80%E5%BC%A0%EF%BC%9A%E7%BD%97%E9%A9%AC%E7%8A%B9%E5%A4%AA%E4%BA%BA%E7%9A%84%E2%80%9C%E9%9A%94%E9%83%BD%E2%80%9D.jpeg)

.jpg)